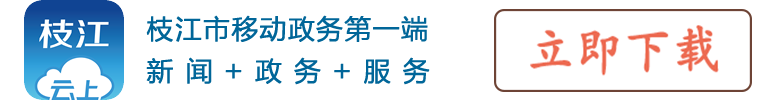欢 迎 收 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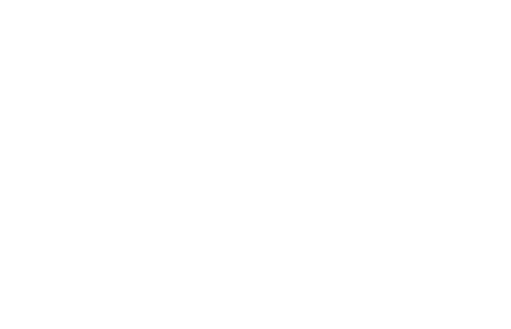
枝江的岛 洲上的梨

枝江有个岛,名曰“百里洲”。
儿时看百里洲,觉得它就是全世界。举目望去,田地是辽阔的,花草是相似的,江堤是宽广的,过江的轮渡好似永远开不出我的视线。
儿时以为,这样的生活会地老天荒。村里的老人临终后都会被安葬在不远的田头。到了夏夜,当萤火虫在墓地飞舞时,大人们纳凉闲聊时会偶尔瞥它一眼,然后自然而然地说起死后的事情,言语间风淡云清,没有丝毫悲伤,让人感觉死亡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大家继续生活。

只有学堂的老师不这样看。
老师时常会跟我们谈起岛以外的世界,会跟我们说当下的日子过得很贫穷,要想办法过更好的日子。
“更好的日子?”年幼的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觉得很是好奇。
”是的,有好多的美食、好多的衣服、更坚固的房子。”老师深信不疑,但他却大半辈子没走出百里洲,所谓的美食、衣服或房子,我们想,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在年幼的我们看来,当下的日子就挺好,有饭吃,有伴玩。我看了一下脚边的大黄狗,深信它是永远不会离我而去的。
在老人看来,当下的日子也挺好,有田种,有饭吃,还有亲戚可以走动,走访最远的亲戚步行一天也可以到达。
“可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呢?”老师说,“做生意!”每当讲到重要话题,他都会言简意赅。“就是卖东西!”
听到这个想法,我们不以为然。因为在这个岛上,四面环水。我们有的邻里都有,不过就是几担米或是田里的一些瓜果蔬菜。米本身就不够家里人吃,即便值钱,一家的口粮也不能卖。瓜果蔬菜呢,我家开花结果时,邻居家也在开花结果。自家都吃够了,谁会稀罕?

可是,我们还是想要过好日子的。这个想法在我们心里就像一粒种子,播下了!
可究竟什么可以拿出去卖呢?我们在家里翻箱倒柜,结果悲伤地发现家徒四壁。我们又房前屋后考察,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有一天,我们发现邻家的老人正站在家里的老梨树下,抬头看着它,且越看越欢喜,此刻上面已经结满又大又熟的梨子。
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一致认为树上的梨子可以卖,因为它们个头大数量还多。而且,百里洲刚开始种梨子的只有三洲村、宝月寺和林场村有零星种植。当我们欣喜的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师时,老师哈哈一笑说,“想法不错,但你们不是第一个想出来的,已经有人往枝江卖呢!” 我们有些暗自神伤,但老师又怕冷了孩子们追求好日子的热情,而后便答应我们,不上学的时候带我们过河进城卖梨。

过河进城,在当时,是每一个百里洲孩子向往的事情。那时候的百里洲,车极为少见,到哪里大家都是靠一双脚,所谓进城,就是坐轮渡去隔江相望的枝江城里头,往返的轮渡从1毛钱、2毛钱……直到九十年代才有了一块钱,一天一趟,早去晚回,好多岛上的人一年到头都去不了两趟。
为此,我们每天放学就蹲守在自家梨树下,要卖梨子,我们自己肯定是不能吃的。若是遇见过往的邻里,特别是那些夸赞梨子好的邻里,我们假装左顾而言它,不再像往昔那样慷慨地与他们分享自家的梨。
终于有一天,老师发话说明天进城卖梨。我们不顾树皮的粗糙,不怕树上的毛虫,勇敢地爬到树上摘,摘了满满两篮子梨,拎到学校,而老师早已经备好了箩筐。

那时候,百里洲的建华村和爱民村(现分别叫三洲村和宝月寺村),因梨子卖难,家家户户都专门定制一种特制的箩筐,长方形的,一担能装上300斤左右的梨子,既可节约运费又方便保管,老师那个箩筐就是如此。至于是他自己编的,还是借的,不得而知。
一大早,晨幕初醒的江堤,橘红的太阳照在江面,照在箩筐的梨子上,也照在我们的脸上。老师挑着担,我们三五个跟在老师的身后,欢呼雀跃里有能坐船去枝江的欣喜,还有卖梨的好奇心。
登上轮渡的我们兴奋不已,当船慢慢驶向对岸,那个我们以为大的像整个世界的岛,变得越来越小。再望望对岸的房子、车子和穿着花衣裳的行人,年幼的我们确信,老师说的好日子是有的!

等到了四码头,那个最早集中卖洲上梨的地方。我们跟着老师,就像是做了错事一样,在集市拥挤的人群里低着头吃力地穿行,我们很努力地在给自己的梨找个好位置,可是所有的位置似乎都有主人,而且别人来得都是特别早。我们很是着急!正在犯难之际,一位邻里向我们热情地招手,他把自己的地方让了一小块给我们。
他卖的是自家种的西瓜,我们与邻里并排站着摆摊,在这里,卖梨的都是岛上的人,因此,我们彼此有惺惜之感。
很多的人路过,总是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但是一问到价钱,便又都纷纷离开。不少人边走边回头看,心里有些不舍,可却总会被身边的同伴强行拉走,“这个梨吃了不管饱,花钱买不值得”,“不就是梨吗,有啥吃头!还不如省钱买肉吃”。我们以为好吃的自家梨,到了集市上才发现别人根本看不上。有些人路过时还会作一番评论,说我们的梨品种太老,皮厚水分少不好吃。那天集市的繁荣热闹并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收获的只有深深的失落。两篮子梨一只也没有卖出去,或许看到我们情绪低落,邻里建议用他的西瓜跟我们换梨,带回去给孩子们吃。出于感恩,我们把最好的梨都给了他。回来以后,我们发现剩下的梨被别人捏得都不好看了,也没有心情吃了。

再后来,我们终于还是选择好好读书,去追求老师口中所说的好日子,家里的梨园交给了父母。待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百里洲种梨子的村子越来越多,新品种的梨子远比旧品种汁水充盈,品相上乘。上门收梨的商贩越来越多,村里的父辈终于再也不用挑着担过河卖梨,洲上的梨有了她自己的名气。
待我在大城市定居后,电商已让那个洲上的梨趟过了河,走出了枝江,我习惯性的每年七月给我的好友们寄上一箱洲上的梨,好友们尝过了,称赞有加,小聚之时,我总会情不自禁的给他们讲起小时候跟着老师卖梨的经历,看得出,他们都听得很认真。
去年过年,回到百里洲,遇上我那年迈的老师,抵面差点没认出我,寒暄一番,询问我近况以后,他问我:“走出去,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啊?”我说:“大家没走出的,这洲上的梨走出了百里洲,不也过上了好日子吗?”继而,我们会心一笑。
现在回头想想,儿时卖梨看似失败,其实极受益,有的是老师希望的,有的则是老师没有料到的。
比如我们再也不会把自认为好的当成世间最好的,就像岛上的人,在尝过新品种的砂梨更甜后,终于选择砍掉老梨树;比如我们会更加努力地生活,在做买卖过好日子这条路走不通时,我们并没有放弃对过好日子的追求;比如邻里会让有限的摊位让给我们,会用他的西瓜跟我们换梨,这一善举让我们从小就明白了助人之心的可贵以及对于他人持有同理心的重要。
出走半生,那枝江的岛,洲上的梨,叫我怎能不挂牵?
来尝一尝百里洲砂梨吧!尝一尝这沁人心脾的夏天,清甜宜人的果香,还有,生生不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