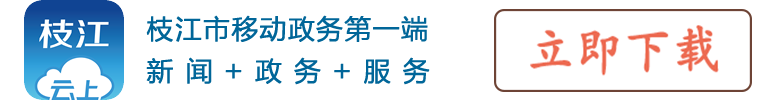欢 迎 收 听

作者 张二林 朗读 泓垚

前几年特别不喜欢和张庆丽说话,我尽可能简短的和她做必须的交流,比如关于父母健康的问题,比如我正怀着宝宝的老婆身体状况,而且多数都是她拨过来,说完重点我就迫不及待地挂掉电话。
当时我的境遇不是很好,偶尔寻求帮助时总能从她言语中捕捉到嘲讽和不信任, 虽然我能消化各种人情冷暧,但真正能伤害自己的,是亲人,同样一句话,陌生人说出来是一片羽毛,但从亲人尤其是自己特别在意的人,就是一把匕首。
如果母亲在电话里问到她,我也不咸不淡地搪塞几句,母亲沉默后低声地说:唉,二林,这是你惟一的亲人,你们小时候多好——
姐姐大我四岁,五岁时就开始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弟弟。
母亲孤苦无援地维持贫穷的家,脾气固执暴燥,喜欢打人,但主要是打姐姐,我只要一开腔她就过来打姐姐,我慢慢捕捉到了这个习惯,稍不满意就张着嘴巴嚎,母亲过来,顶着两个冲天小辫的姐姐免不了受一顿打。
经常挨打的姐姐倒不怎么哭,六岁的她已经能跑过母亲,只是在跑的时候还是习惯性拖着我,所以被撵得四下逃窜,看到母子仨依次奔窜的场面我很快破涕为笑,十分努力地跟在姐姐后面,母亲听不到哭声也不再追,拎着树枝在远处恐吓,说再听到弟弟哭今天晚饭都没得吃。
即便我一天都不哭,依旧很晚很晚才能吃到饭,母亲性格极为好强,即便是种地,她也不希望落在邻居后面。黄昏过去了很久,我们家厨房依旧是冷火秋烟,母亲正勤劳地收最后一垄高粱或是挖最后几窝土豆。
我和姐姐饥饿难耐,她拽着我倚在邻居的门框,流着口水盯着邻居的饭菜吸吮自己的大姆指,我趴在地上目光不及桌子高,寂寂无声地看着姐姐。
母亲收工时若刚巧见到这个窘迫的场面,会小跑过来粗暴地拎着姐姐的耳朵拖回到家里,摁跪在稻场中间,母亲言语凌厉强蛮,把很多不曾有的缺点悉数扣在姐姐头上。
我端着碗立在姐姐身旁,希望她哭几声或是认下错,姐姐好像不再饿了,绝然不哭,站起来几脚把我踹开,自己又跪回了原处。
直到上小学,姐姐才不再因为我哭而挨打。
她习惯把头发剪短,套着表哥穿旧后的灰色夹克,比同龄男孩子胆子还大,我们自留田边有棵毛桃树,从认识它起就不曾结成功过一颗果实,好几个比姐姐大的男孩子都被她摁在树下,问是不是他们偷了桃子。
五年级后姐姐去桥坪小学寄读,周六才回家,从太阳刚升起我就盯着崖口子,等待姐姐的身影出现,崖口子是卧在村边的一道小山岗,距我家有好几里地,即使她们一行有好几位同学,我依然能准确快速地分辨出姐姐的身影,雀跃得一路小跑去接她。姐姐把她在学校没有吃完的咸菜瓶递给我,我用小木棍探进瓶底,咂着嘴满足地舔木棍头上粘附的油脂。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能帮母亲干活的年龄,尤其是寒暑假都要下地去干农活。姐姐不是一个好帮手,从未按母亲的指令去执行,她点的高粱出苗时像国画初学者的作品,地这头几十株浓墨重彩地挤在一起,而另一边则是大量的留白,放的土豆种更是隔好几尺远才出一株苗。
母亲在地里补救时顺手削好了柳条,不过姐姐对挨打有了很强的预知,她已经非常会爬树,母亲离家还有几丈远,她已经上到门口水桶粗木梓树的顶梢,月亮只能从她脚下升起,母亲围着树骂累了回家拎来斧头,作势要把树放倒,母女斗争结束时圈里的猪都已经饿得没了声响。
这段在清泉村生活的光阴温情而具体,只是时间慢慢掌握了山里的气候变化,开始熟练快速地向前推进每个季节,母亲的柳条还未折断,13岁的姐姐就去了更远的付家堰中学读初一。我希望时光能压实或是厘清回忆:曾经的艰难,充满温度的过往,我用心捕捉回忆时涌动出的各种情愫,促使我记录下这一段真实温暖的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