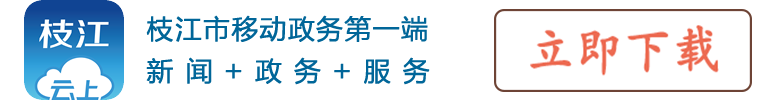天亮鸟鸣,窗外的绿意渐渐渗进吊脚楼,罗长姐缓缓撑起身子,掀开被褥,先抖抖鞋口,再看看鞋底,确认没有异物后才穿鞋,把透明的薄袜抻直至熨帖肌肤,最后用布条缠包头发,有条不紊。
整理完毕后,她凑近上了铁闩的木门,轻声招呼:“儿子,起来,起来,起来吃饭吧,小政,小政,小政,起来吃饭吧”,唠叨中带着柔顺。

罗长姐与儿子祁才政。
这是纪录电影《罗长姐》的开场。导演金行征近年来秉持着“拍摄中国正在消逝的老村”的想法,将镜头对准那些无言的残破老村,为观众掀开世界一景的图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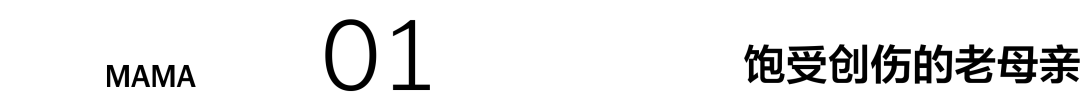
在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罗长姐每天都要给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祁才政料理日常。
祁才政是罗长姐的小儿子,1968年参军,1974年在部队服役时得了脑膜炎而失忆,自己穿衣洗漱都成问题。罗长姐从此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张罗小儿子的日常起居,兢兢业业,不肯马虎。

每天早晨天不亮罗长姐就要起来给儿子准备早饭。
每天,伴着鸡鸣猪哼,罗长姐将田地务农得来的土豆放进铁锅,端一小凳,守着灶火,看着铁锅里咕噜咕噜冒泡的吃食,靠着门,大半身子埋在晦暗的静默中,似乎镶嵌进背后斑驳的墙壁。只有随意搭放在腰间的双手,伴着呼吸轻轻起伏,泄露了老人自己都没注意的心事。

直到灯光被大儿媳亮起,罗长姐才回神,整个人像上了颜色的油画,开始活动了起来。
虽然她的眼疾日益严重,已经看不清东西,却还是耐心而仔细地将煮熟的土豆铲成泥,颤颤巍巍的手在大儿媳的帮助下将三块肥美的猪肉放进碗中,最后不忘体贴地淋上一些肉汤,端到小儿子面前。这样一做,就是四十七年。


上图:四十七年来,罗长姐一个人担任起照料儿子的重任。
下图:趁着儿子还算清醒,罗长姐赶紧给儿子洗把脸。
祁才政失忆后还保持着部队的生活习惯,整天披着军上衣,早上按时“出操”,巡逻着自己的场地。
罗长姐将吊脚楼右边的绕间用环形栅栏围住,入口小心拦住,隔着栅栏,轻轻问道:“宝宝,你饿了没有”。

隔着栅栏罗长姐与儿子祁才政在灶火前生火。
年轻的祁才政脾气暴躁,整座山都是他捶打木门的声音。如今他也逐渐老去,牙齿开始脱落,总是自虐式地打自己耳光,表达自己难以传递的情绪。
罗长姐只是默默地看着,不肯放过孩子在她眼底的每一个时刻,没有害怕和难过地躲开,只是慢慢说着“不打,不打”。这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仍是一种柔软的状态。

吊脚楼屋里屋外的物件上都萦绕着罗长姐生活的痕迹:挨个播撒的土豆,苞谷地下一路延伸的贝母,分批按捆整理好的柴垛,耐心熬制的糖茶,缸里熬制的豆制品,新生的小猪。走进这个家,就能看见一个农村妇女如何用生活细节维持着一个普通农家的平凡却不平淡的生活。
几十年来,罗长姐像一个不停周旋的陀螺,运转的动力和外部的鞭策都来自祁才政。照护祁才政是这些沉默而清楚的家事里必不可少的一环,是罗长姐生活的底色。

每天半夜,罗长姐都要细心察看儿子的睡觉情况。
差不多五十年来,罗长姐将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楔子,用它来尽量扩大团团围住祁才政的生活的断裂。只是缝隙越来越大,或者不如说,罗长姐用自己铸成的保护墙不再那么坚固了。她有时一天都坐在躺椅里,让时间数着她的白发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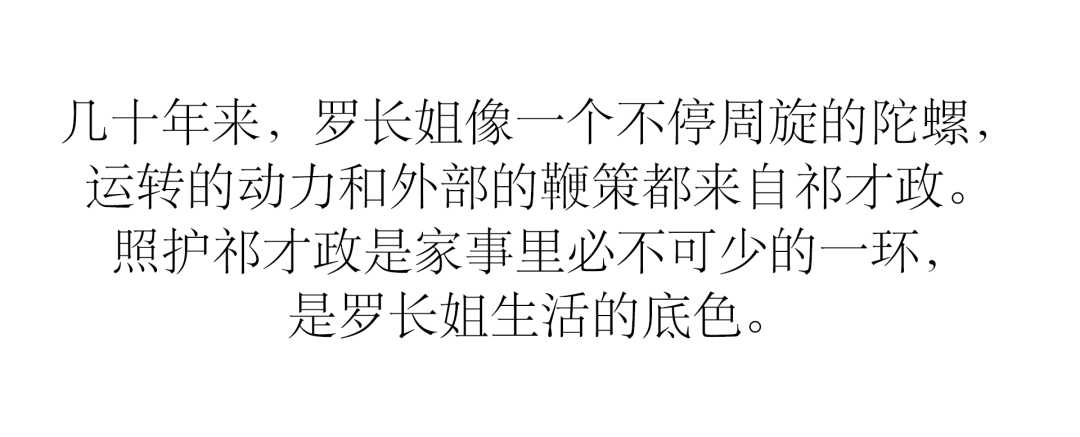
罗长姐决定将祁才政托付给孙媳妇刘文芳。屋檐下,两个人做着农活,一人轻描淡写地讲,一人安安静静地听。
岁月增长带来的不是伤痛而是静观的距离,罗长姐不避讳照护的辛苦,事无巨细地交代着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吃饭要煮熟弄软,穿得要干净整齐,床上要暖和干净,洗澡理发需要多喊几声,锁好门。生活的勇气和行动的意志在这场交接仪式里传递,一个新的“罗长姐”即将出现。

孙媳妇刘文芳正在帮祁才政洗衣服。
这些吃穿住行的叮嘱,罗长姐原本准备是交给细心的孙子祁文勇的。2015年3月,祁文勇在工地上放炮,被掉下来的石头砸死。
提及逝去不久的孙子,罗长姐少见地落泪了:“我虽然不在小辈面前流眼泪,但背地里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我没有哪一天是过得愉快的。”
似乎是有所感应,平日暴躁失常的祁才政低低地探出了头,哽咽地说着囫囵的话。乡村生活的截面下是少有人知的情感肌理。


上图:有时祁才政会说一些囫囵的话,罗长姐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下图:1986年,罗长姐60岁时,在村干部的证明下,和大儿子立下字据:如果我不在了,由大儿子负责照顾才政,大儿子60岁后,交给大孙子照顾,一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时不时会有以前的战友前来看望祁才政,讲讲他当年被调到军区后,给司令员当警卫员的神气和威风。战友隔着栅栏,用褪色的黑白照片,给他指认故人的离去,得到的总是祁才政紊乱的记忆和离去的背影,最后叹气道:“你这人啊”。
罗长姐发现,祁才政能和穿着军装的人好好说话,能用部队的搪瓷碗筷好好吃饭,也乐意穿着军绿色大衣。


上图:祁才政入伍时和战友的合影。
下图:罗长姐时不时会拿出儿子当年的照片捧在手心来看。
不久后,早上那声“儿子,起来,起来,起来吃饭吧,小政,小政,小政,起来吃饭吧”,换成了“二叔,二叔起床了”。
大多数时候,这座吊脚楼都是沉默寡言的。包裹它的时间也变得慢吞吞,被罗长姐和祁才政的身体凝固,封存,化作标本。过去的生活好似脆弱的枯叶,没有汁液也没有胶质,稍不注意就被时光碾出清脆的声音。

自生病回来后,祁才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栅栏中度过。
对着光看去,只能看到时间赋形留下的叶脉网络,细小而易碎,用力回想才能想象出原本那娇嫩欲滴的模样。
屋内,祁才政已经习惯刘文芳的喂食。刘文芳穿着跳跃的红色进进出出,阳光很好,她回屋内换了另外一件同样喜人的红色外套出门。屋外,晒着太阳的罗长姐慢慢站起,在屋檐暗影的遮蔽下,消失在转角处。


天气较好的时候,母子俩会各自出来晒晒太阳。
平凡的人既如尘埃,又与宇宙共悲欢。罗长姐的家人清楚每个季节的鸟叫声,能分辨哪个月会来什么样的鸟,唧唧切切,如断如续。这些声音预示着生活的苏醒和自然的复原。群山之间的呜啼合唱,在树篱和小丘上纵跃,撞击着每一个在其中生活的人的心。生活在其中的人,时间充裕,世界宽广。
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罗长姐在接受采访时很骄傲地说“再艰难也不找政府”。这份底气来自一年四季辛苦耕种的韧性。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自己的土地,依靠天时人力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鸟鸣啁啾,春暖花开,秋收冬眠,土地与人互相依赖,酝酿出农村的四季轮回,孕育出罗长姐照护儿子的顺应自然和她那颗全然专注又全然开放的柔软的心。这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活着的东西内里柔软,外在坚硬。

虽然年岁已高,但罗长姐至今仍然可以自己完成家务劳动。
然而,这种乡村生活也是中国正在消失的生命世界。导演金行征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你知道吗?在2002年,中国还有360万个自然村落。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锐减至270万个。十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落,一天消失250个。”在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体系里,那些被忽视的群体该如何在被遗忘的空间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纪录电影最后,晒着太阳的罗长姐慢慢站起,在屋檐暗影的遮蔽下,消失在转角处。《罗长姐》诚实地展现了农村女性身体和心灵所累积的痛苦,以及这些痛苦带给她们的被动负重。在传统农村的归属体系里,女性的生存方式一般有未嫁从夫,既嫁从夫、夫亡从子、年老立命四种。
罗长姐是年老立命的”老祖宗”,刘文芳是既嫁从夫的孙媳妇。刘文芳取代了罗长姐成为忙前忙后的主角,也接过了罗长姐背负的生活意义。对于罗长姐而言,生活的意义不在别处,就在每个活生生的当下。她全然对生活敞开,没有缴械投降,也没有束手无策,在贫瘠的现实里她给了精神病人无法用金钱获得的爱与尊严。

夜色中,罗长姐在大儿子的搀扶下消失在转角处。
当生命意义的交接来到下一代,乡村对于孙媳妇刘文芳而言,不知是羁池还是有待耕种的土地。根据 2000~2015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长期从事照料活动的农村妇女被诊断患有慢性病的概率提高 9.8%,而自评健康较差的概率显著提高 17.6%。导演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好多人就疑问:她的孙媳妇为什么要接这个任务?我们只是想表达,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在农村你想改变是很难的。”在调查农村生存状况的《梁庄十年》里,作者发现农村女性生活在家暴、偏见、歧视、流言与各种权力体系下,女性很难拥有主体性。这是我们的文明话语内部的一个痼疾。
时代洪流下每个人都有无法避免和无法逃避的外部裹挟,女性如何在受限的生活经验,在家庭组织的伦理结构,在乡土生活的思维惯习中,勉力在动荡中扩展自己的经验世界。
纪录电影没有也无法给出答案,或者说,在解决问题之前更重要的是展现问题:无数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相关,而农村的女性经验是理解这个消逝的世界的一种方法。
来源:“故乡与世界”微信公众号